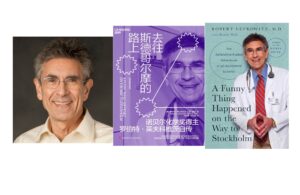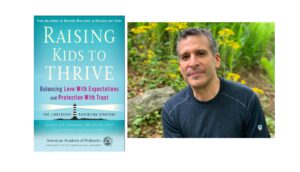刘瑜 2011 年有一个演讲,讲到自己的学思历程。后来这篇演讲被总结成文字,非常好看。(详见《刘瑜:我的读书历程》)
虎嗅的李岷在这个总结文字前面写了一段:
“刘瑜的读书几阶段,特别典型地勾勒出 70 后稀里糊涂一片空白长大,而后突然发现擦世界长这样啊,然后在无大师引领只下自行嗅探,读哪算哪儿悟到什么算自己造化的头脑之旅。”
非常到位。
刘瑜学的是文科,上大学是 90 年代初,还有一点 80 年代的尾巴。我上大学比她晚三年,又读的是理科,所以如果刘瑜那时候是一片空白,那我只能说是一片惨白。
她说那时候高中看的书就是习题册,不仅四大名著没看过,连武侠和言情小说都没看过,以至于她上大学,同学以为她是外国回来的。
看到这一段笑死。因为我也差不多。
记得在清华的时候,有一个很文艺的师兄来做阅读调查,问大家都读什么书,花多少时间看书。我彼时正在备考 GRE,腆着脸问,GRE 阅读算么?因为我只有时间读这个。
其实 GRE 阅读,也没有“读”,看做题的套路而已。
现在想起当年的那个文艺的师兄,都替他为我汗颜。可怜的他,以为进了清华的就有文化。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是没有。后来越来越明白,学习好和有文化完全两码事。进清华的肯定都是做题家,是不是读书人就另说了。至少我不是。
不过刘瑜说:“其实说一片空白是不准确的,应该说是负数。”(“空白”对那个时期都是一种美化,因为“空白”意味着你至少没有“中毒”。为什么这么说,大家自己点链接看。)
对比一下,我“负”得更深。而且很多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看不是课本的书,特别是讲什么历史、哲学、思辨的书,不仅没有用,还浪费时间。记住历史书里讲的背过能考上就行了。不是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么,我为什么需要看这些?
后来发现,很多理工科的都和我差不多德行,哪怕去了国外名校拿了博士做了教授,也只不过在自己的领域进得深一步而已,通识缺失的。我想对我这一类人,有个很好的概括,就是高学历,没文化。
- “我来参加作文比赛”
那些年如果有一点点亮光,是初中翻我妈的书,看了《茶花女》和《红与黑》。不记得怎么在家里写字台的橱子底下翻出来这两本书,只记得《茶花女》是坐在写字台旁边的地上一个下午看完的。
那时候我是“好学生”,但说实话,对学习,特别是对文字,是没有感情的。
有多没感情?
我小学被老师送去参加作文比赛。比赛在一个教室里,黑板上挂了一张春天的彩图,让我们写。我记得很清楚,我下笔第一句写的是:“我今天来参加作文比赛”。我也没觉得有问题,直到“比赛”结束以后,和我同去的同学问我怎么开头的,我理直气壮地说了我的开头,然后问:“你呢?”他说:“我开头第一段是四个字,阳春三月。”
我才知道,原来不应该开头写“我今天来参加作文比赛”。
你笑了吧?嗯对,用现在的话说,不是一般的尬。
但是那天看《茶花女》,跟着故事,到最后哭得不行。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书掉眼泪,现在还记得我坐在小屋子的地上看书的那个角落,第一次感受到的文字的力量,是那个没文化时代的一点点的闪光。去年我看徐晓的《半生为人》,中间好几次哭得不行,放声大哭那样的哭。真的感受到好的文字传递出来的人最深层的痛苦和无奈,是直穿人心的。
最近一次掉眼泪,是看孩子的一本书 The One and Only Ivan,书是给孩子写的,讲一个被关了 27 年的大猩猩的故事。整本书都是非常简短的句子,但构建起来的故事却层次丰富,直达人心。那些表面的幽默和轻松后面的无望和压抑,那些监禁、伤痛、死亡和希望,就这样通过一个个短句构建出来了,我看到后面也是哭坏了。没想到写给孩子的书,文字也能如此穿透。
扯远了,这些都是后话。
回到我的不读书史,以上是第一阶段,“我今天来参加作文比赛”。
- “从 PPT 了解世界”
清华毕业到美国读博士,读了很多 paper,英语水平提高不少,也写了不少 paper。但每天泡在实验室,除了做实验、看文献,没有别的时间。既然这么忙,也是没空读书的。继续有学历,没文化。
后来到麦肯锡,读了很多内部“PD”,就是行业文件,看各个行业的数据、概况。觉得知道了很多知识。各种数字、对比、行业发展历程,说出来头头是道。而且那时候也开始自大,觉得我做了这么高级的工作,获得的知识肯定比书上要先进啊,似乎更没有读书的必要了。而且,通过 PPT 了解世界,一会儿饼图,一会柱图的,高效直观得多呢。
不仅通过 PPT 了解世界,慢慢发现,自己也只有对着 PPT 才能讲话。去开会,没有个PPT,怎么开,说啥?
那时候拿项目需要去竞标,经常做 100 页的 PPT 标书“砸”客户。开会的时候标书每一部分讲什么都是有路数的、有一次我们讲完了 PPT 以后退场,一个本土咨询公司进来,总共放了一页 PPT,合伙人上去侃侃而谈了一个小时。
我那时候惊呆了,一方面似乎有足够的资本对这种“不专业“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心底觉得:哇好牛啊,这个本事很厉害,没有 PPT 给我一个小时,真不知道讲什么。我得重新获得这技能,讲话要扔了 PPT 的拐杖。后来练会了,不过这是后话,以后有机会和大家讲。
这个阶段的光,其实和业务无关,是在麦肯锡认识的那些人和他们的故事。2013 年参加的合伙人培训,让我知道一位资深合伙人,两个孩子都在 9 岁左右先后癌症去世。看他的状态完全不知道他经历了这样的至暗人生悲剧。而且他讲这些经历的时候从来不哭,说自己的女儿生前特别爱笑,所以自己决定要把女儿的笑带给这个世界。他在上面讲这些经历,下面所有的同事都在呜呜地哭。几个大老爷们哭得最响。那个夜晚的哭声,忘不掉。
- 40岁后,开始读书
2015 年进入公益领域,因为需要了解公益领域,知道这个领域的顶级学者是资先生。看了书才知道,她不是研究公益的,曾经是社科院美国所的所长。但是在研究美国的过程中了解到公益慈善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而做了相关的研究,出了多部相关的书,也成了公益慈善领域屈指可数的专家。从她的《二十世纪的美国》开始,我才开始真正的读书之旅,现在想想,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
后来因为做一土教育,开始读陶行知,了解 100 年前的海归知识分子的教育实践。本来是当历史读物读的,毕竟是百年前的故事,但读了才发现,那一篇篇小品,讲的哪是历史,明明是当下。那时候似乎是民生凋敝的旧社会,但很多记载,现在看来都让人羡慕。
一篇简短的《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是 1924 年写的,里面有几个学校的小故事,每一个都生动可爱,充满了一个民间教育者构建的教育场域里那令人敬佩和喜爱的气质。其中一个故事是丁校长在关帝庙里办学,带着学生和当地村民合作,解决校舍问题。
“丁校长于是开始偕同教员学生合力改造学校,改造环境。校址是在一个关帝庙里。关公神像之外还有痘神、麻神等等。这些神像已经把课堂占去了大半个。
丁校长一方面要教课堂适用,一方面要免去地方反对,就定了一个保存关公搬移杂神的计划。他就带领学生为关公开光。把神像神座洗刷得焕然一新,并领学生们向关公恭恭敬敬地行礼。他再同教员把这些杂神的神像移到隔壁的庙里摆着。他们又把那个庙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这些杂神安排得妥妥当当,大家也行个礼。
杂神搬出之后,这个课堂又经过了一番洗刷,加了些灰粉,居然变了一个很适用的教室。村里的人看见关公开了光,杂神安排得妥当,又听见学生报告向神行礼的一番话,不但不责备校长,并且称赞校长能干。”
彼时我们正在为学校场地发愁,看到这一段就想,现在哪怕能找到这么一个关帝庙,也是绝没有办学校的可能的。
北京的蝌蚪实务学堂,关门之前目标是服务在北京务工人员的中学年龄的孩子,为社会培养“珍贵的普通人”。教员都是志愿者,大家志愿来教课。我想要是陶行知还活着知道他们做的事,也会很喜欢的,也会有这样一篇文章。学堂刚开始招生的时候,团队在城中村的电线杆上贴广告留了电话号码。等了两天,终于有人打电话,但不是学生家长,是城管,在电话那头说“再贴你们有麻烦!” 如果陶行知还健在,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从陶行知这条线开始,了解那个时代的人。陶行知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教育,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还有胡适。在费城的有林徽因和梁思成。林梁我们似乎都熟悉,但是真读书才知道大众媒体里看到的无非是他们生命历程里很窄小的片段。从 50 到 70 年代,梁思成经历了什么,只有只言片语,可那是足足二十年。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写了一本英文书 Liang and Lin,这么多梁林的粉丝,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本书。我看了,跳跃的文字下,有一种哭都哭不出来的压抑。
和林徽因同时代的,还有合肥四姐妹。那个合肥现在也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不读书,恐怕不知道安徽合肥曾经是这样一个风水宝地,孕育了这样一个书香门第。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的丈夫是创造了汉语拼音的著名学者周有光。
周有光在 106 岁高龄出版了《拾贝集》,里面是一篇篇小品。推荐大家都看看,风趣幽默,处处真知。
其中一篇说苏联的解体之后,俄罗斯共产党的书记久加诺夫认为瓦解的原因在于“三大垄断”,即苏共“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
还有一段叫“浅层原因”。说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研究苏联瓦解的深层原因,访问了多方面的人物。他访问一位工厂工人,这位工人说,我不懂“深层”原因,只懂“浅层”原因。很简单——贫穷,落后,残暴,自命最先进!
从这些人的作品开始读,一本到另一本,才慢慢知道“有文化“的人看到了什么,写下了什么,也知道为什么有文化的人发不出声音,没文化人的在四处呱噪。当然这没文化的人里,有一个是我。
- 大雁粪雨
到这里就不能写了。
因为只要开始读书,很快就发现,在有些时代,读书史可能成为犯罪史。我们还是轻松一点,看看《拾贝集》里这篇小品——大雁粪雨:
“1969 年冬天,我随我的单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人员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里原来有二十来个劳动改造站。国务院有十几个直属单位连同家属,共约一万多人,占用其中两个站(“一站”和“二站”),我们单位分配在“二站”。在那里劳动两年四个月,这对我的健康有好处,我的百治不愈的失眠症自然痊愈了。
在那里两年四个月中,最有趣的记忆是遇到“大雁集体下大便”。
林彪死了,“五七干校”领导下令,明天早上 5 点集合,听报告。早上我一看天气晴朗,开会到中午,一定很热。我就带了一顶很大的宽边草帽,防备中午的太阳。
快到 10 点钟时候,天上飞来一群大雁,不是几千,而是几万,黑压压如同一片乌云。飞到我们的头上时候,只听到一位大雁领导同志一声怪叫,大家集体大便,有如骤雨,倾盆而下,准确地落在集会的“五七战士”头上。
我有大草帽顶着,身上沾到大便不多。我的同志们个个如粪窖里爬出来的落汤鸡,满头满身都是大雁的粪便,狼狈不堪。当地老乡说,他们知道大雁是集体大便的,可是如此准确地落到人群头上要一万年才遇到一次。我们运气太好了,这是幸福的及时雨。我们原来个个宣誓,永远不再回老家。林彪死了,不久我们全体都奉命回老家了。”
嗯,我们运气太好了, 这是幸福的及时雨。